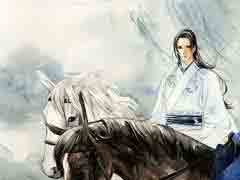姜衡琢磨了一会儿,径直去了北辰殿,让宫人都退下了。
元泰帝还在批奏折呢,休假大半年了,一时间猛然把奏折拿回来批,还挺累。
“怎么这时候过来了?郑无疾肯放你走?”
姜衡围着元泰帝转了两圈,在元泰帝要发火的前兆前,扒在了桌案上,“你们不对劲!”
元泰帝头都没偏一下,可有可无嗯了一声。
姜衡:?
“我都问您了!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这样不对。”
“嗯?”
“无论是君臣,还是父子,这样藏着捏着都不对,会出大问题的!”
“嗯……”
“君臣父子重叠了,出问题概率更大了!”
元泰帝终于捏了捏眉心,“怎么?你还是想要补上一次请陛下称太子?还是称陛下?”
姜衡有点扭扭捏捏了,“也……也不是不行……”
元泰帝:……
元泰帝放下笔,“你二十了!”
“还没满呢!”这些大人就爱讲虚岁,什么过年就算一岁,那一年岂不是就涨两岁了?干嘛非要叫老了?
“二十了,也是弱冠之年了,别再毛毛躁躁的。”
不过,虽然理论上来说,二十才是弱冠之年,但其实每个皇子封王的时候,别管到没到二十,都算提前及冠,能独立主事,当家作主了。
“知道了知道了,大事上我很稳重的,”元泰帝口风一漏,姜衡也知道这段时间异常的原因了,但他可不会拒绝,不仅不拒绝,还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,“那父皇,您真不后悔啊?”
元泰帝左手开始揉了揉右手手腕,姜衡也不要一个后不后悔的回答了,再不跑,后悔的是他,“咳,东宫还有事儿,儿臣先走了,您慢慢批,慢慢批!”
没揍到人,元泰帝深深呼吸了几次,“都是倭寇的错!”
“都是倭寇的错!”
东宁省,尤其是以琉球群岛为主要区域的军营之中:
“若非倭寇,我们早已回归中土,若非倭寇,我们早已得到朝廷的帮扶,若非倭寇,我们早就过上了好日子!”
“儿郎们!我们要跟随中原的将士,诛杀倭寇,还我安宁!”
“诛杀倭寇——”
“诛杀倭寇——”
朝堂上:
“倭岛,承我中原典籍,却不尊教化,以怨报德,屠戮沿岸百姓数百年,此为一罪!”
“妄称天皇,此乃二罪!”
“我朝以德报怨,只废黜其皇位,予其王冕,然其依旧野心不改,攻略我东宁琉球之地,至琉球百姓死伤数万,更意图分裂琉球,夺我国土,此乃三罪!”
“此三罪,无一例外,皆是诛其九族之大罪!”
“臣请出兵倭岛以剿贼!”
“臣附议!”
“臣附议!”
“臣等附议——”
元泰帝自龙椅起身,俯瞰朝臣,“准。”
桩桩件件,没有一件,冤枉了倭岛,至于时间有偏差,有什么偏差?琉球不一直是中原的吗?他们分裂琉球,杀害琉球百姓,冤枉他们了?一点没有!
屠岛的人,自然依旧是许本,屠岛的争议,也自然是武定侯和他这个开国皇帝来担。
即使真相百姓心知肚明又如何,正史上,就是在元泰朝,武定侯屠的岛灭的国,与太子无关。
大梁,会有一个全然仁德的圣天子。
第57章 传位
仁德的太子,奉命主持了大军出征前的祭祀仪式——祭天(类祭),祭地(宜社),告庙,祭军神……
史官对此,迟疑片刻,还是在元泰帝的眼神中,没有具体描写出征前的祭祀场景。
要史官说,这次的祭祀仪式,还真是给足了倭岛面子,不写也好,一笔带过就行了。
“不写?凭什么不写?你是史官,你怎么能屈服在强权之下?!”
史官:您现在就没有使用“强权”了?
“那臣在野史里写?”
这下,懵逼的反倒成姜衡了,“你都不装了?”
“……臣不知道大梁故事的作者是否是臣,但臣可以是。”
不要怀疑他们史官的文学素养好吧?
姜衡仔细琢磨了一下,他知道元泰帝此举是好意,想要给他塑造一个好名声,不过干倭岛诶,他也不能干看着啊。
于是姜衡鬼鬼祟祟跟纪文说:“把孤写得强势一点,你看孤,都节制天下兵马了,许本也是孤的人,懂了吗?”
纪文;他不太懂,为什么太子殿下总是执着于给自己名声抹黑。
“臣懂了,您放心。”
野史也要写两本了,一本传出去,一本糊弄上司,或许这就是打工人的宿命吧!
作为史官,还是更希望本朝有个“圣君”的。
姜衡向来相信文人的野史能力,满意的回到了东宫。
如今,就等将士们凯旋了!
这次,许本虽然没有历练七年之久,却也在沿海历练了三四年,还有徐忠将军亲自带着,效率全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加之曾离还跟着去当了军师,又有改良版带火炮的战船,新式火铳,及一应严格检阅后才配备的弓箭雁翎刀等冷兵器装备,郑无疾与郑国公主亲自盯着操持的后勤,只会成功的!
东宁省,琉球群岛,最北方的大岛之上,是守卫东宁海防,和随时准备听从命令,反击倭岛的将士。
高丽,驻使馆中的官员友好的与高丽朝堂磋商,确保高丽不会反水坏事,高丽却表示,他们只想立功进步!
他们,也眼馋倭岛的利益。
这是一场,属于倭岛的围剿。
这是一场,值得各方,各国,严阵以待的战役。
却也是一场,诸国心知肚明结果的一场战役。
“倭岛能撑多久?”
“撑不了多久吧。”
“就是不知,大梁会如何处置倭岛。”
“檄文上说的是,大梁已经废黜了倭岛的天皇之位,贬为王位,倭岛却不知感恩,不思悔改,侵略东宁琉球群岛,意图分裂大梁国土。”
“这罪名不小。”
“是啊,我估摸着,倭岛也会变成一个省,如果大梁的气儿没消,可能省都混不到。”
当中原这只沉睡的巨龙睁开双眼,开始认真,他们想象不出来,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岛,该怎么抵抗。
且,虽然倭岛盛行下克上,但中原大国与他们的差距,连他们自己都知道,强行对上,犹如蜉蝣撼树。
就像现在,当沿海驻守的士兵,看见海面上,飘扬着的大梁旗帜,一字排开的战船,心里第一个想法便是——完了。
大梁,竟然真的打来了!
火炮的攻击距离尚且有待改进,但弓弩与射手,也足以让倭寇避之不及。
铺天盖地的箭雨,掩盖住了倭岛的太阳。
猛烈的炮火,将城墙击倒。
“儿郎们!能否加官进爵,就在今日了!”
“杀——”
身为大梁的儿郎,又怎么可能没看过天幕?
倭岛上面是倭寇吗?那是一个个的仇人,是军功。
“报仇!”
“报仇!”
“诛寇报仇!”
血色在倭岛蔓延,那是烈阳的颜色。
而这样的攻势,并不只在一方。
当东樱王自以为牵制住了朝堂,为此沾沾自喜,还沉浸在温柔乡里之际,前线传来的噩耗,直接让其傻在了原地。
“不可能,不可能……”
大梁若要出兵讨伐他们,去年何必多来一遭?
幕府……
幕府?!
他们说的是真的!
“他骗我!”
“中原人都是骗子!”
什么礼仪之邦,什么大国容量,都是假的,假的!
“大王!快逃吧!他们已经追上来了!”
“士兵呢?护卫呢?都是死了的吗?”
这才多久?!怎么可能就要追上来了,他们现在可是在国都!
国都——破了。
大樱的旗帜——倒下了。
在倭岛有人得知天幕,得知倭寇被屠的那一刻起,倭岛的命运,注定只能是重复天幕中的结局。
倭岛上,一片惶恐,倭岛外,何尝不是各方担忧?
他们迫切希望早早得知倭岛的结局,他们需要了解,大梁的态度。
以及——或许能够借此机会,小小窥探一番,中原王朝的实力的一角。
可这一等,就是两个月。
“怎么这么久了,竟还没一点消息?”
倭岛沿海,全是大梁的战船在守着,他们根本不敢就近打探。
他们只知道,看这架势,大梁没有任何意外的赢了。
但是——后续呢?
怎么两个月了,还没有一点动静呢?
可当真有动静了,他们宁愿收到的消息是假消息。
什么叫:倭寇誓死不从,主将许本不得不下令屠岛……
屠岛……
没有皇帝的授意,哪一个主将敢私自下令屠杀降国,什么,你说人家没投降,屠杀是不得已?都是千年狐狸,玩儿什么聊斋呢?
离得最近,原本想要分一杯羹的高丽朝堂更是集体一个腿软。
“真,真屠了?”
“真屠了!”
惊惧,惶恐,失声……
忽的,一声尖锐的鸣叫响起,“怎么会屠岛?!何至于屠岛?!”
他们倒不是同情可惜倭岛,而是,中原王朝这个向来遵守和平的国度,怎么会如此光明正大的屠岛!
他们之前还说愿意襄助大梁攻克倭岛,可他们一直以为,攻克日本,也就是把人家打一顿,抢一些东西,教训教训,中原王朝自古以来,不也教训了他们几次吗?
可现在教训到直接屠岛了!
那下一个是谁?
就因为一个只有中原人能看到的天幕吗?
当中原王朝不再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,周边的国家,又会是怎样的未来?
此刻,高丽无中生有的,不知道谁给的自信心,突然就碎了。
随着大梁军队的返程,倭岛就此成为历史的消息炸花儿似的往周边扩散,中原的外藩诸国,接连陷入了恐慌之中,无比慎重的就如何对待中原宗主国这一命题,进行了严肃的讨论。
而中原宗主国,此刻,正处于一片欢腾之中。
元泰帝为大梁的好儿郎们论功行赏,升职加薪,以庆这累世之仇得报的喜悦时刻。
当然,到许本这里,元泰帝直接照抄了弘德帝的答案,加封为武定侯。
直到最后,才是倭岛,也就是现在东平岛的后续发展。
没错,东平岛,也就是一个岛而已,别说行省,连正规的府县之称都没一个。
“启奏陛下,东樱王有负皇恩,习幕府之恶,征调役夫,强掳矿工,日夜不停,以开采银矿,臣秉承陛下与太子之教化,已将他们救下,安置与东平岛上,数十万民夫,皆泪泣我中原皇恩。”
“大善!”
史官提笔速记,大梁,大德啊!救数十万民夫于血海啊!
至于这些民夫之后的结局?不是怕他们水土不服,还专门在东平岛上重新给他们找到了工作吗?还都是做惯了的手艺活,还要有什么要求吗?他们中原,还不够仁善吗?
如此,君臣齐心,默契的详简结合,很快就进行到了下一场,庆功宴。
而在庆功宴的最后,元泰帝起身:除了刚归国的将士们,其余官员也默契起身,心想:来了。
“朕开国平天下至今,已二十有四年矣,至明年,也到60了,愈发的力不从心。太子知节守礼,心怀仁德,堪为仁君。”
“朕,将于九月初五,传位于太子,颐养天年。”
太子大惊失色,“父皇折煞儿臣,您正直壮年,儿尚且年幼,如何扛得起这九州万方?天下万民都有赖父皇啊!”
“正因你年轻,朕还能再帮衬着你几年,莫再推辞了,钦天监已经看过日子了,九月初五,大好的日子,就这样定了!”
虽只有一辞,但三,本就是一个虚数,三辞三让,没问题!
周边的国家,一个个更是麻了。
高丽与安南,是亲自证实过天幕,知道弘德帝就是太子的,也见识过百姓对弘德帝这位奇葩圣君的态度的,只道是元泰帝屠国有些太狠,太子看不过去了,顺势夺权上位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,只等太子继位后再去朝拜一次。
毕竟,中原王朝皇家的父子关系,这太正常了!
但是除开安南和高丽,其他国家就更慌了呀,信息差太多了!
“之前废过一次太子的元泰帝传位于新太子?”
“还是在刚刚屠了一个岛国后?”
“中原王朝,有皇帝主动退位的吗?”
“……李渊?”
“我说主动!”
“……”
“这可是手握兵权的皇帝。”
“可这位太子好像也节制天下兵马……”
“但他没战功,战场都没见过,如何指挥得了元泰帝的将帅?只靠一个兵符?”
“会不会……元泰帝这个杀胚还想灭国,但是……”
但是不想担责毁名声了?
一个自己打天下的开国皇帝,和一个深宫长大,捡漏太子之位的,没有及冠之龄的小儿,谁是灭国的凶手,还用考虑?
“大梁态度不明,琉球倒是发展起来了,可琉球王一家都在京中做人质困住了,倭岛灭国,安南高丽南吴都有驻使馆,态度暧昧……”
“我们也该去朝贡一次了,不能再拖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?”
“九月初五来不及了,先递申请吧,由大梁决定时间。”
南方诸多小国,彻底忙碌了起来。
而北方,北蒙几个大部落的首领,也再次聚集在了一次,只是这一聚,这才发现,短短两年,他们这些个部落首领,一个个竟然越发富态了起来。
此时此刻,他们不是看不出中原的险恶用心,但是他们能强硬让底下人不养羊不赚钱吗?那么多钱啊!
一旦逼迫底下人停止养羊,停止互市,不止部落的高层,就是奴隶,也不能忍受,高层不能再忍受草原的穷困,奴隶不能忍受,冬衣稍微暖和一点的严冬。
他们,中计了。
偏偏明知中计,却找不到破局之法。
“元泰帝这个老鬼,竟然要传位当个太上皇,你们信吗?”
“呵,信个鬼。”
“怎么办?”
“高丽那边有驻使馆,他们连见面都不敢,纯废物。”
“再去一趟中原,看看那皇帝老儿,究竟在玩儿什么把戏!”
各方势力,皆看向了中原。
元泰廿四年九月初五,元泰帝传位于太子衡,本欲与众妃嫔退居行宫,新帝言岂有父避子之理?仍居东宫,尊太上皇于北辰殿,至纯至孝,堪为孝子表率。
第58章 一生行善弘德帝
“哪儿有皇帝住东宫的?他们中原自古就讲究一个名正言顺。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,这小皇帝,定是傀儡无疑!”
上一次,草原派出去的使臣巴图,换来西域彻底被收复,草原陷入经济制裁,巴图已经失去了草原首领的信任。
即使巴图拼命表示太子真的权势颇大,能越过皇帝直接下旨,但没人信他,因为听起来太荒谬了。
故而,新皇帝住东宫的消息一传来,那些首领,只会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“糊涂啊!”
东宫很差吗?东宫的规格不就是小一点的一整个前朝和后宫吗?
当东宫里住着实权皇帝,那东宫就是真正的皇宫。
可惜,没人信他。
又或许,他们只是更愿意相信大梁内部不稳罢了。
其余的藩国就与这些草原部落首领想的不一样了。
大梁刚刚灭了一个国,太上皇也好,新皇帝也罢,都是能决定他们生死的“皇”,纵然人家内部有争斗,也不妨碍人家都能灭了自己。
待大梁的批复下来,允许他们来朝贡,贺新君继位,一个个都觉得活了过来,还能商量,挺好。
至于是明年过年之后,他们理解。
毕竟——周边的国家还不少,一个个接待,不如一次性接待,省得麻烦,而远一点的范围,就需要一定的传播消息的时间。
而对于大梁来说,新帝登基,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不大,对于朝堂而言,也同样不大,毕竟,权力的过渡,已经过渡了四年了,早习惯了。
唯一激动的群体,就是考生这一群体了。
明年正式改元,是为弘德元年,开设恩科,这一次,经业书院兵家学院已经施行了起来,故而,文举武举并行。
“武将培养难,文臣却一茬一茬不断,文武举并行,如此,也避免了文臣的独大,单脚走路终究不稳。”
“这第一批武举出来,进兵家学院的学生,我要去坐镇看着!”太上皇不可否认,当继承人足够放心,安心养老,人都精神了不少,这一闲下来,就想找点事儿干。
倒是登基后的姜衡,再也没法轻松摸鱼了。
当太子的时候,上头还有皇帝顶着,能心大的甩手,可一登基,元泰帝干脆的真的退居二线,光是责任感,就没法让他再放心摸鱼。
闻言,哀怨地转头看向一脸红光的太上皇,“您本来就是经业书院名义上的院长,还是太上皇,没人拦着您。”
“说正经呢,想培养什么样的?那群老家伙们能力不用担心,但是培养学生不一样,尤其是培养武将,马虎不得。”
“忠君爱国,思想不歪,其他的,看他们的造化。”
太上皇了然颔首,不再多问,直接就离开了北辰殿。
是的,北辰殿。
说是新帝住东宫,但没住到一个月,太上皇就带着太妃们搬到了前朝留下的行宫之中,景色还比皇宫里舒坦,若非武举一事,太上皇还嫌回来麻烦呢。
如此,父慈子孝的天家美名,也都有了,可谓双全。
看着太上皇潇洒的背景,姜衡不禁有些怀疑,提前继位,真的有必要吗?
有的有的,包有的,在位时间能多好几年呢。
当然,这是几十年后的事儿了,现在还有一堆要处理的事情呢,光是科举,就不仅是一个武举的问题。
“东宁省与西域的考生,还没有能考到举人参加会试的,但毕竟是陛下登基的第一年,臣私以为,不能不顾两地的情绪。”
“但若是破格录取,或者破格让其参与会试,他们可没有足够的实力让其他考生服气。”
“且有一就有二,那以后的北蒙呢,不说北蒙,就是相对贫困的海南呢,若他们也要破格,朝廷怎么办?”
就东宁省与西域的考生问题,诸位大人切磋了数轮之后,终于得出了一个能让所有人暂时统一的,并且符合正规程度的方案:
国子监名额。
虽说现在有了经业书院,但是国子监的地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,经业书院偏向于学术,而国子监成绩达标后,是可以毕业,直接授予官职的。
所以,可以对西域和东宁省本地的考生,根据他们自己当地的水平,走“贡生”的途径入国子监。
为表君恩,只需要多开放几个监生的名额,这边合情合理了,谁也说不出错来。
弘德元年的科举需要考虑的问题,便提前给完善了。
“倒是说起海南,海南偏南,朕看这次递交朝贡申请的外藩中,有地势与海南相似之地,他们的一些作物,未必不能在海南试着种植试试。”
同一纬度上,相似的气候条件,海南这块宝地,有的是发掘的地方。
“臣等明白。”
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,很快就到了新的一年,提前了几年的——弘德元年。
外藩的使臣也陆陆续续,抵达了大梁京城,被安排在了驿馆。
草原这次的代表换了人,没再让巴图来,阿古拉受草原几个大部落首领的影响较大,潜意识受到了影响,觉得新帝是个傀儡,没太在意巴图的提醒。
阿古拉一到京城,就去拜访慎侯,打听太上皇的喜好和风格。
慎侯:?
看在曾为草原同胞的份上,慎侯好心提醒了一句,“你不打听当今陛下的喜好?”
然后,就看见阿古拉一副也行的样子,看似礼貌道:“您说。”
慎侯:……没救了!
大梁的过年,是从除夕到正月十五的,在这期间,是不上朝不当值的。
也就这次他们来的时间早,要接待外藩,这才让部分老大人,鸿胪寺官员,和驿馆的官吏忙碌了起来。
为免错过朝贡,藩国大多选择宁愿提前到,于是,这些藩国使臣,可以说是在京城,过了一个年。
也见识到了,过年期间,中原王朝的繁华,加大了他们要继续与中原王朝贸易的决心。
只是不知,如今的大梁,到底是何态度了。
直到正月十六,朝廷才开始接待诸国使臣。
因来访藩国众多,直接举办了大型宫宴。也避免了朝堂上,更为严肃的氛围,让外藩使臣们,能心情放松一点点:他弘德帝,一生仁善,跟屠国,没有半毛钱关系的!不用怕的哈!
此次宫宴,太上皇并没有出席,所有外藩使臣见到的皇帝,只会是年轻的弘德帝。
也是在此刻,阿古拉才陡然一惊,新帝绝对不会是傀儡皇帝!
如果太上皇贪权掌权,又怎么可能在有诸多外藩使臣的情况下退居幕后不出面?
巴图的话,如今响彻在阿古拉脑海中,阿古拉糊里糊涂的遵循本能,面君见礼入宴,和周边的使臣一起假笑举杯示意友好。
外藩使臣一个个的,依次献上贡品与贺礼,而从始至终,弘德帝都言笑晏晏,看不出半点不耐,十分具有亲和力,全然没有一丝杀伐的气息。
他们想:弘德帝,应当不会举起屠刀吧?
献礼完毕,姜衡人模人样笑道:“诸位的心意,朕都知晓。”
“之前几年,倭寇一直骚扰我大梁沿海,为百姓安全,不得不暂停海贸。如今倭寇已除,我朝,自然欲重开海贸。”
姜衡话音一落,各使臣身旁的翻译也随之译完,当然,大部分使臣自己就能听懂,早已从自家六王子那里得到一点消息的安南使臣立马出列,面上惊喜道:“大梁陛下圣德!有朝廷作保,海贸定安然无恙,大梁与我等藩国,也定能共同繁荣!”
其余使臣,也听懂了意思,弘德帝意在开海,发展海贸,倭岛是特例,只要不阻止海贸,大家一起做生意,就会安然无恙。
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事儿?
别看他们都是藩国,可藩国与藩国之间也是不同的,甚至是相互欺负的。
像中原王朝这种,只要和他做生意,或者只要朝贡,认他为“宗主国”,承认这个“名”,就能给予庇护,又不欺凌小国的王朝,那真是大海捞针般的难找,至少如今,只有中原王朝一个能做到这样。
中原王朝实在是太体面了!
如今中原王朝将要求明明白白说出来,他们还有什么害怕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