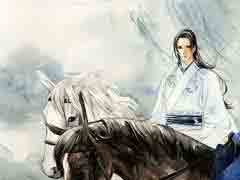元泰帝自然不会平白无故给人定罪,但心里不舒服是真的,要让臣子知道他不舒服,也跟着不舒服,也是真的。
【一份手札,是给后人的遗产,保了大梁两百年的平稳;
三种作物,是给天下的遗产,植根于土地,扎根而生,再度延续了大梁两百年;
大梁四百年,以至于后世的现在,鹤仙的那份给天下人的遗产,依旧在生长出可口的美食,填饱我们的肚子。
史书工笔,真假难辨,然,功业永存,谁对百姓好,百姓会记得。
他是大梁太宗文皇帝姜衡,也是一心修仙,却修出大爱的九天无垢纯灵净世度尘元鹤仙君。
自他以后,再无皇帝,敢言自己求仙,因为求仙的例子,是姜鹤仙,再没有皇帝,能做到姜鹤仙的功绩,能做到姜鹤仙那样,又不在乎功绩。
太宗皇帝长眠于阳陵,元鹤仙君卧云于仙庭。】
“大梁……四百年……”
虽然得知大梁灭亡了,可,四百年……
“够了……”
元泰帝的声音,轻到连旁边的郝大珰都没有听清。
两汉也才四百年,大梁四百年,够久了。
姜衡则在想另一件事,四百年,弘德一朝,已经在开始海贸了,发展海上政权了,纺织行业也出现了高效率机械了,资本主义萌芽是必定的。
而且那阿婆主说的,大梁四百年,到后世的现在,中间没有提其他朝代,之前的太祖茶话会,也是在大梁就结束了,所以……
所以四百年后,没有皇帝了!
是个好消息!
王朝该灭国就灭国,皇帝该消失就消失,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干了!
这一期视频的后劲很大,但好处更大。
虽然冒出来个僖宗丢人,也说出了大梁的结局,但无论是增产的粮食作物,还是天幕还没有细讲的天花,仅这两样,只要太子还活着,还在太子的位置上,足以保证大梁的民心稳固。
不过这些,都不是马上能拿出来的。
现在天幕刚刚结束,无缝衔接需要讨论的是——宗亲的教育问题。
“太子,你现在可有想法?”
朝臣也一个个盯着太子,他们现在没什么争权夺利的心思,太子要是能一次性说完,反倒不用他们动脑了。
姜衡还真有点想法,反正不能学某家那样养猪崽,“儿臣现在是这样想的。”
朝臣舒坦了,有想法就好,不用折磨他们。
诸王屏气凝神了,这关系到他们以后的孩子了。
“读书是要读的,读书明智,明理,他们身为宗亲,纵然是不能袭爵的子嗣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依旧是高山,无法翻越,所以,书是必读的。”
朝臣们满意地颔首,是这样的,宗亲就是好好管束,不能让他们祸害百姓。
“所以,儿臣的想法是,五岁之前,在家里各自启蒙。
五岁到八岁,统一上课,文学基础,武学基础,琴棋书画等艺术基础,在这三年都学一学。
三年之后,根据擅长方向分班,文,武,才能,各择一而精学。
正好经业书院也快建成了,到时候,光是一个文,就够他们挑选的,不怕他们想学。
至有志之年,不再强制学习,是袭爵,是考取功名,还是做个文人墨客,亦或靠着余荫过完一生,都由他们自己选择。”
朝臣们表示这个好,元泰帝这个长辈自然觉得更好,太子可太孝顺体贴了,愿意额外花这么多钱培养宗室,学习好啊!学习了,出去才不丢脸!
诸王也觉得还不错,学多点东西总没坏处,只有楚王,不可置信地看着姜衡,这么紧的学习任务,五岁就开始让人卷,你忘啦你自己就逃课啦?
还到有志之年(15岁)后可以自己选择,你忘了你十三就跑出宫逃离学堂了吗?
姜衡自然察觉到了楚王那露骨的视线,眉梢一挑,“六哥,又苦不到你,你慌什么?”
元泰帝闻言瞬间眉头一皱,眼神一凛,刺向了楚王:怎么?有意见?
楚王:……
“没……没意见……”
他一个不事生产靠着父皇和九弟过日子的,敢有什么意见啊?
而且,九弟说得也不错,他都已经当爹的年纪了,这些新的宗亲教育新规出来,也管不到他头上,至于自家儿子,也是为了他们好不是?
元泰帝收回视线,继续看着他的好大儿,好大儿还在表演,“还有一点,无论以后宗亲们是否入仕,在少时学习的过程中,思政的教育必不可少,这是所有人都要学的。”
“思政?”
“对,思政,思想政治教育,他们是宗亲,由天下百姓供奉着,不强求他们担责任,但至少要教会他们不能乱来。”
朝臣闻言,更是大力表示支持,这个想法可太好了,这些天潢贵胄要是捣起乱来,谁都不好做,太子能有心规劝宗亲,这是天大的好事啊!
“殿下大善!”
当然,新规也不是嘴皮子一张,就能这么定下来的,基础的课程有哪些,怎么根据擅长方向分班,这些都是要细细研究的。
至于交给谁拿出细纲……
“此事,便交给宋祭酒,孟学士,与卫国公共同商定。”
祭酒宋明章,自然是代表文臣;孟家后人,翰林学士孟怀书,新一代儒家代表,此时在这儿,同样也是各传统学派,经业书院的代表;武勋集团代表李建勋,自然武将一方的态度。
三人一起拿出章程,这样的结果,对各方都好。
而皇子皇孙,甚至是太子的教育方案,就需要元泰帝和太子再开一次小会讨论后,再拿来说,哦不对,或许还要加一个冤种前太子。
“你们父子不觉得你们很过分吗?”
“二哥,你不能把你摘出去,你也是当儿子的。”姜衡义正言辞。
“呵呵,我觉得我是给你们当孙子的。”
安王忘记了,姜衡向来混不吝,只见姜衡认真思索了一番,“如果二哥能返老还童,我也不介意当二哥的爹,这样太孙也有了。”
元泰帝竟也被带偏了思路,顺着这离谱的想法想了下去,“还真不错,老二吃过一次教训,想来也不会再被朝臣牵着走,还有经验,稳定性确实比未知的太孙靠谱。”
“……”
“如果没事,我回去睡觉了。”
“青天白日,睡什么觉?晚上睡不着?不都让你戒酒了吗?”
废太子那几年成习惯了,哪儿能轻易戒得了?
安王没说出口,只转移话题道:“皇家要培养出能教学生的老师出来,我看小十一就不错,小十二……小十二就算了,让他跟着老四吧。”
安王的意思是,以往的皇子教师团队,先继续用着,总归太子至少还能活五十多年,他们也有五十多年的时间,来慢慢培养。
而年幼的宗室子弟,还尚且不知这一噩耗。
北辰殿里在开小会,散会的朝臣们呢?
工部主要官员去了户部,增产的良种啊,实打实的救命的良种啊,天下百姓都等着我们的海船呢,总之一句话,给钱!
兵部的也有人去了户部,良种在等着我们呢,海军的训练迫在眉睫,还是一句话,给钱!
国库的钱就那么多,户部还能凭空变出来不成?
要是谁来都给钱,那户部也干脆别要了。
郑无疾也不客气,自己挡着不说,还把赵王周王两个亲王拉了出来挡着,二位殿下都在户部挖墙脚了,总不好意思再不帮忙吧?名义上两位殿下还在户部干活儿呢!
赵周二王只能顶上。
赵王却还不知,赵王妃已经进了宫。
赵王妃温涵,是与元泰帝一起打天下的谋士之一开国功臣崇康伯之女。
与赵王已经成婚五年,将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,赵王不冒尖不出头,她在妯娌里也低调,与其他王妃相处和谐,少有主动进宫表现的时候。
这次进宫,也不是给赵王生母宋昭仪请安,而是直接面君。
“老七家的?那应该是有要事,让她进来。”
显然,元泰帝对儿子儿媳还是很了解的。
“我回避。”安王起身准备避开。
其实哪里用得着安王回避,大梁的礼教还没有严苛到如此地步,只不过是安王想要趁机溜走而已。
总归宗室教育的想法也大体出来了,元泰帝也就默认了安王的遁走。
温涵此时来,定然是国事相关,大概率是与塔娜相关。
果然,是塔娜看到了天幕,并在天幕透露出天花后,说出了想要写信给家里,让部落早日归附的话。
“儿媳以为,当时的塔娜或许是真心,但不可尽信。”
“哦?”
关于塔娜的资料他们早就已经拿到,但相处中的感觉,又是另一回事。
如同资料中,塔娜是受尽宠爱的四公主,但姜琦却觉得,这位四公主性格不像是很受宠的,毕竟,一个受尽宠爱的公主,会在异国他乡感到轻松吗?
此时,他们也想听听赵王妃的判断。
“塔娜渴望得到认同,夫君的认同,我的接受,侍女们的认可,焉知不希望得到部落中其他人的认可。”
赵王妃比姜琦年长几年的经验,让她看得更加明白,有时候,受宠的孩子,反而没有过的不好的孩子用着放心。
至于塔娜漂亮?无论在哪儿,美貌单出都是死局,真心疼爱的受宠,与单纯利用的受宠,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更别提还在王室之中。
而现在,塔娜要写一封劝部落归附的家书,希望王妃帮忙送到部落之中。
“照她的意思帮她写家书,让她自己签个名字或者盖个章。”
至于会不会让部落误会,那就看部落是什么反应了。
他们不会赌塔娜在家书中接夹带私活的可能性,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密码本之类的。
也通过这次,让一些部落知道天幕的存在,再威慑一番。
对于不能自己书写家书,塔娜没有第二条选择,只能表示感谢。
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完了,没想到在临冬时节,赵王妃温涵再次进了宫,不过这次,是先去的东宫,毕竟正常情况下,皇帝只看最后一道的结果,更别提现在太子早已名正言顺的监国摄政。
“七嫂来了?御厨琢磨出了新的菜式,待会儿叫七哥过来一起用膳?”
姜衡本人本就较为随性,温涵又是他嫂子,私下里,姜衡自然不会闲得慌摆太子的谱。
“行,这次可能还真要他也一起忙。”
“嗯?户部出事儿了?”原本放松的姜衡一下就来精神了,不至于吧?
“那倒没有,不过户部歇不下来是真的,九弟你看这个。”
那是一团白色的……
姜衡瞳孔一缩,这是——棉花?
不止这一小团可以捏的蓬松的棉花,还有一块塞了棉绒的布。
“这不临近冬天,也该做冬衣了,塔娜那儿也在做冬衣,但我发现了这个,塔娜说这是他们漠西的棉花,北蒙反倒是没有这个的。”
“我看了看,比南方种植的棉种,保暖效果要好一些。”
棉花,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种植记录,也就是“白叠布”,“桐华布”,像是在姜衡原世界,元朝明朝都曾大力推广种植棉种。
当然,现在的棉花,自然比不上后世的棉花,现在的棉花,其实多为木棉,纤维较短且易碎,但作为填充物来进行保暖,已经足够了。
贵族自然不缺少一个棉花来保暖,但无法发声的,更需要保暖的,永远是百姓。
就像南方其实也是有棉种的,只是品质没有漠西,也就是西域之地的棉种好,即便这样,也不是百姓能轻易享受的。
“等等,漠西……我记得塔娜他们部落,现在是不是在天山以北?”
温涵点头,“他们之前曾占据西域。”
“也就是说,我们攻占下来的大半西域上,本就有这棉花。”
“是的。”
这可真是,守着金山银山而不自知。
“是我的问题。”他早该想到还有棉花这玩意儿的,在纺织业那一期,他就该想起来的,怎么就忘了呢……
温涵没想到姜衡会直接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,“这哪儿能怪九弟,四哥和朝堂公卿都还没反思呢。”
话虽如此,可有些事儿,只有姜衡自己清楚,他本该想到的。
但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,“这事儿多亏七嫂心细,不然大梁,可真是损失重大。”
“本就是一家人,应该的,倒是还有一件事,也有这个有关。”
姜衡耐心听温涵说明,生怕他不知道棉花到底是怎样的,“这花看着白净,可最开始是有籽的,脱籽,弹棉,纺织,这西域地区,棉花虽不少,可因工序复杂,能穿得上棉的人,其实也只有部落中的贵族。”
虽然中原也一样就是了。正所谓: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。
所以,如果要推广西域的棉种,光是种植区域扩大,是不行的,工具的改良,才是重中之重。
棉布不同于丝绸,是为了给底层百姓保暖的,所以研究的进度,越快越好。
西域的棉种,值得如此对待。
“我明白了,就麻烦七嫂帮着写一道折子了。”
温涵笑得更真诚了,哪里就用得着麻烦了,这是在给她机会表功呢。
不过如温涵一开始所说,户部的赵王怕是不好歇着了,不仅是赵王和户部,工部,兵部都一个样。
收回来大半的西域更多是军户在那边驻守屯田,和兵部分不开的,种植棉花,也离不开军户。
至于户部,更不用说了,原本的草原人民,现在的大梁子民,光是户籍一道他们就轻松不了。
以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拨款。
得知消息的赵王匆匆赶来,满脸兴奋,这可是白来的功绩!
哎呀,九弟这婚指得妙啊!让老八当时还一脸看戏,嘿嘿,现在酸了吧?
周王酸没酸先另说,晋王先挨了一顿批,数落张掖侯的折子也往西域发去了,驻守陕西的秦国公也没落着好。
“就是当时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?后来呢?驻守西域已经一年了,难道原本的夷人,一个都不在乎棉种?”
“他们原先是夷民,现在也已经是大梁的子民,中洲迟早要一统,草原也早晚要归附。我们是汉人,但他们才几个人?草原才收复一半,你们都做不好接纳,以后呢?啊?全靠太子戳一下你们动一下?”
“草原的归心,难道是靠兵刃一亮,嘴皮子一张就完了?”
元泰帝发了大火。
在元泰帝看来,这已经不是简单的,没发现棉花的失误问题了。
而是从骨子里轻视漠视了归降的草原部落夷民,而这,与中州一统的国策,是相悖的,如果大梁的军队将士,一直是此等姿态,那不利于万民归心。
草原的子民不是傻的,你面上的态度都不做好,如何让人家相信你,从而拱卫大梁的四方?
连大梁四方的夷民都不能归心,又如何让远方的番邦相信大国的包容与气度?
“还有你们!”
元泰帝又指着文臣,“不是说着让外族也沐浴王化,学习中原文化吗?派去西域的臣子在那儿待了都快一年了,怎么也没传回来棉花的消息?是他们还不会中文吗?是他们还对我们防备心重吗?”
“臣等有罪。”
皇帝都气得骂人了,还狡辩啥呀,先认罪等皇帝消火了再说吧。
“有罪,呵,认罪倒是快,法不责众嘛,朕还能全给你们贬了不成?一个个的,在朝堂之上,嘴皮子多利索啊,到了西域,就哑巴了?”
等元泰帝骂得差不多了,姜衡这才适时站了出来,“父皇息怒,这棉种虽好,可棉籽不易脱落,手工繁琐,普通的百姓难以穿到棉衣,不主动提及,恐是怕再次白白做工,倒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“而南方的棉种,也不普及,迁移过去的百姓,军户等也都是北方人,忽略掉了西域的花一样的棉种,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“中原与草原,本就磕磕绊绊千年之久,双方之间本就有这血仇,仅一年,就要求双方和平融入,的确有些为难人了。”
“朕看他们就是不用心!”
“父皇此言差矣,西域寒凉困苦,将士们与先生们留在西域,何尝不是忠君报国,一腔热血?又岂会不用心?”
说完,姜衡给了左相一个眼色。
左相顺势道:“未能让两地百姓早日融合,是臣等之过,臣有一计,或可补救。”
“说。”火发了,太子红脸唱了,他也该顺势冷静了。
“回禀陛下,棉种不止西域才有,可唯有西域的棉种最佳,但原本西域的百姓却享受不到,不若工部早早改进机械,提高棉纺织效率,让西域百姓第一批穿上棉衣,从而真正打破双方的隔阂。”
吃不饱穿不暖,读书又有什么用?
读书太高级了,对西域底层百姓而言,也太快了,他们需要的第一步,是能安稳的生活下来。
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元泰帝也终于放过了朝臣。
下了朝,姜衡却没有回东宫,而是走到了左相身边,“丞相,孤还有一个想法。”
“殿下您说。”
“好事不能白做了不是?”
聪明人不需要多说,左相一瞬间就明白了姜衡的未尽之言。
草原的贵族多坏呀,草原的冬天可是能冻死人的,底层奴隶为其劳作一生,也穿不上一件自己做出来的棉衣,中原的王朝多好啊,让他们能避开寒冷的冬季,穿上暖和的冬衣……
就问是不是事实吧!
不仅要在西域传遍,还要往四周传,将大梁的仁德,实实在在的传扬出去。
经济战要用,舆论战,也要用。
引起这一系列事情的塔娜与乌日罕主仆二人,却对此还一无所知。
但没多久,秦国公与张掖侯这对父子,先后收到了宫里传来的申斥。
秦国公驻守陕西,这件事其实和他关系不大,但张掖侯驻守在西域,这么大的一个疏漏,他这个张掖侯的亲爹,又怎么能脱得了干系?
农桑农桑,他们军户屯田,倒是只顾着田了。
秦国公甚至亲自到了一趟张掖,“怎么一上任就这么大的疏漏?你别给告诉我军队里没一个人发现棉种。”
那不现实。
天山以南的西域回归之后,军户会屯田,可同时,这部分区域也不仅仅会有军户,总会有为了土地迁移到此地的百姓,虽然比不上中原,那也是土地。
所以这片区域,也不仅是士兵,不止男子,怎么可能无一人发现棉花的用处。
张掖侯也头疼,“我已经了解清楚了,不是没人发现棉种,但是大伙儿都忙着种地开荒。”
没错,虽然这里原本是有主的地儿,但对于中原百姓而言,还是得重新开荒一次。
“这棉种效果如何,百姓不清楚,但仅仅是脱籽,就太废时间和精力了,加之那些部分夷民对棉种有些抗拒,百姓就觉得,搞这棉种吃力不讨好,怕沾染晦气。”
张掖侯没有深说的是,天幕之后,百姓的民心是稳了,但有时候,总会思维拐向奇奇怪怪的地方,让他们完全不信玄学,不可能的。
秦国公听明白了,但,“那也是你这个做主将的失误。”
“我知道,这么大的教训,足够让我清醒。”
“那就好,只是你说部分夷民,还有部分呢?”
“还有部分倒是不抗拒,与之相反,他们表面上抗拒,暗地里宣扬棉种不好,实则悄悄屯起来,自用保暖。”
“所以,陛下没有骂错,你甚至没能让夷民开始信任大梁的百姓。”
秦国公面不改色,直接作出决定,“朝廷有了计划,你好生办好,等戴罪立功后,请辞侯爵。”
张掖侯没有反驳,也没有多问,“是,儿子明白。”
令行禁止,秦国公能深得元泰帝信任,作为功勋之首,靠的绝非仅仅是军功。
见次子脑子清醒,秦国公跟着巡视了一番军营,在结合朝廷的任务给次子梳理了一遍,便不再停留,连夜赶回了秦地。
第二天,张掖侯便聚集了张掖之地的百姓,有迁移来的,有本地,还有军户,都聚在了一起。
“诸位,今年初秋,原本部落的塔娜公主嫁给了赵王。”
张掖侯语速说得很慢,自然是为了如今的南西域夷民能够理解,当然,翻译也必不可少,保证大家都能听懂。
虽然,他们不明白这个将军突然说这些干嘛。
“塔娜公主得沐汉家文化,回想部落中的同乡,心生怜悯,她告诉我们,西域生长出来的棉花,可以帮助百姓度过寒冷的冬季。”
“棉花?就是那白色的?他们夷人不是嫌弃吗?”
迁移过来的汉家百姓骤然对西域本地百姓怒目而视,“好啊,黑心肝儿的东西,果然蛮夷有别!”
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
他们汉语本就学得磕碰,自然解释也不能快速的解释。
“不是什么?我看你们……”
“安静!”
张掖侯示意士兵维持纪律,汉人百姓心中有火,他们之前嫌弃棉种是一回事,被隐瞒又是一会儿,他们气儿不顺!
西域本地百姓担惊受怕,根本不敢起反抗的心思。
“只是曾经,只有部落的贵族才得以享用,西域的百姓为奴为婢,却得不到一点温暖,如今,塔娜公主深感曾经的错误,试图弥补,故而献上了棉种的种植方法。”
汉人百姓脸色一红,五彩斑斓,再看西域百姓一年了仍单薄的身形,好像闹误会了……
这么一想,当初劫掠的蛮夷,可不是他们这般模样,而如今这些夷民,不过是原本的“奴隶”罢了。
草原的部落,本就是更为落后的奴隶制度。
“陛下与太子仁德,塔娜公主为赎罪而献棉种,允诺以后的孩子封王,作为西域重回中原的桥梁。”
“朝廷也已经在研究脱籽等程序的机械,致力于让大家都能有衣过冬,在研究成功之前,因西域的诸位曾有经验,由大家选出几位巧手,教导众人……”
而后,便是相应的待遇等内容。
“西域已经回归中原,我们大梁一视同仁,万望诸位一起,早日研究出棉花相关的纺织机械……”
汉人百姓误会了曾经为奴为婢差点死了的夷民,夷民得到了汉人给的机会,双方沟通促进的桥梁,这不就有了吗?
而塔娜与乌日罕主仆二人,仍旧无知无觉,就这样,到了新的一年。
大年初一,天幕再次亮了,这一次,却不是阿婆主的声音,而是……吟唱声?
第43章 第九期视频
一声像是从远古而来的吟唱自天幕中响起,天幕的视频中,竖起了火把,而后,是跃动的鼓声,与那旷远深邃的吟唱声相和,心脏,没有缘由的,跟着频率跃动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