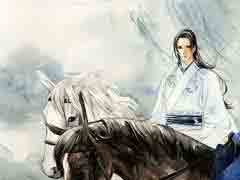“这什么话,我们学成文武艺,不就是为了报效国家吗?怎么还成我们的不是了?”
“不是儒生,难道还是法生不是?秦用法可是灭国了的!”
这不能不急啊,他们学儒学了十几年了,要靠这个考科举的,要是真不用儒了,他们不是白学了吗?
这可是实打实的切身利益相关。
而真正聪明的,在孔家被抄家,太子举办百家文会后,就早已察觉不对,如今,不过是尘埃落定。
【启朝以前,是世家的天下,启太宗一朝后,世家颓废,印刷术得以发展,同时将科举发扬光大,提拔寒门等底层读书人,以权衡没死绝的世家。
思路是没问题的,但在官场竞争上,他们是对立的,却并不代表,所有情况下,他们都是对立的。
科举的兴盛,同样带动了士绅的崛起。他们和世家,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区别。】
【儒学也好,圣人也罢,不过是他们加强话语权的,手中的泥塑,任他们揉捏。
就像启朝某位儒学理论大家,还活着的时候,他的理论被人诟病,死后,理论便被刻意曲解,被尊崇成了大儒、贤者,因为死人不会辩驳。】
“这不是玩儿不起吗?”
大街上,有商贩听着觉得有意思,一不小心将自己想法给秃噜了出来。
旁边的书生闻言,脸色涨红,“你个不读书的,你懂什么!名家经典,本就有不同的理解!”
是我们儒生的问题吗?分明是为了服务君主,君主怎么能背刺我们呢?
【可满朝都是儒士,天下皆是儒生,鹤仙又能怎么破局呢?
就连元泰廿一年黄河案后的山东,孔家也不过受了一点皮毛伤害。
有人造反可以镇压,可文化思想的侵蚀,无声无息。】
可偏偏,太子已经通过“暴力手段”,给打开口子了,提前了天幕不知道多少年。
文人学子,世家子弟,纷纷等着天幕揭露答案,他们自己也在推演,若是自己,该如何做,可再如何思考,他们也觉得如今儒学太势大了,难不成再来一次黄河石像?
【弘德十六年。】
“这不是你定太子那一年?”时间是不是靠得太近了?
在元泰帝的心里,既然已经是变法不得不妥协,所以立太子了,那就应该暂时稳一手才对。
毕竟小九在儒家上面,本来的想法就是慢慢来,所以,十六年这个时间点,是不是太早了些?
而且还有一点他很好奇,是对儒家出手了,再立的太子,还是刚立了太子,就对儒家出手?这前后关系,还是很重要的。
【鹤仙在年初定下了太子,因鹤仙要清丈田亩,改革税法等造成动荡的朝堂,总算是看似稳定了下来。】
所以是刚立太子,小九就马上拿儒家开刀出气?
你这……难怪人家登上皇位就想追封亲爹呢。这样一来,谁都清楚皇帝对太子是没什么好脸色的,太子日子能好过?
看来,太子能安稳登上皇位,忍功还是了得的,怪不得后面憋不住了呢。
哪怕偏心的元泰帝,此时也不得不承认,废帝是有点子苦的。
【这一年科举,殿试的题目,全是鹤仙一个人出的,而这一届的科举,也是考生最倒霉,最不好答题的一届科举。】
“莫非是出了法家或者其他学派的题目?”
“我听闻当今太子重实践,莫非全是要实操的题,没有纯理论的?”
“不过既然要对儒家出手,那肯定没有儒学的内容,考生可不倒霉吗?”
然而天幕马上告诉他们,全都猜错了。
【鹤仙重实用型人才,往年的科举,不论哪个出题官,都会顺着鹤仙的意思来,尽量避免纯理论不会办事的进士。可偏偏,这一年的殿试题目,鹤仙全出的理论题。】
天幕上放出了三道大题,能看懂题目的人,要么傻了一样待在原地,要么冥思苦想,要么化身乐子人,还有的当场将题目抄下来准备破题,这可是真题啊,是太子的偏好啊!
不说破题破得难受的学子,就是钦明殿的臣子,都觉得头疼,这叫什么?
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。”
【阿婆主这里简单翻译总结一下。
第一道题,是问考生,董仲舒说天人感应,荀子说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,那该听谁的呢?】
荀子是先贤,董仲舒是后人,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,已经成了“君主”告罪的“圣书”,要说天人感应错了,荀子的才是对的,岂不是要自己放弃儒生的一把利剑?
【第二道题相对就简单了:孟子说: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,何解。】
这……意思简单,但好答吗?
【第三道题没有矛盾点,问:如何理解荀子的师法之化,隆礼重法。】
【三道题,全是理论题,擅长背书的学子们也是有福咯~】
能进入殿试的,有不会背书的吗?这根本就不是会不会背书的问题,而是没有一道题是好答的,这是答题吗?这分明是学子站队,是要命!
【据说当天殿试结束,学子们身子看起来都很虚弱。】
姜衡则是觉得,自己还是没下狠手的嘛,这几道题,是有些为难人,但除了第一题,后面两道题还是很好糊弄考官的不是?
他又不可能真靠一个科举就完成对“儒教”的打压,不过是开胃菜罢了,至于那么害怕吗?
看着太子那轻松写意,还带着意犹未尽的神色,百官又觉得前途无“亮”了,天真的要塌了啊!自己还能跳去哪家来着?殿下似乎中意法家?
【这一届的排名都是延期了几天才出的。但最精彩的,还是早朝,鹤仙的操作上。】
【当阅卷官一个个战战兢兢,犹犹豫豫,把握不准皇帝的心思的时候,鹤仙作为贴心的君父,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,不用担心,科举只是吓吓你们,实战在朝堂呢。】
百官笑不出来,这样的贴心,有些让人担惊受怕了。
【鹤仙就说,前些日子给考生出题,翻阅了先贤经典,深受洗礼,觉得先贤们说得都太有道理了,所以呀,朕有一个想法。】
你还是别有想法了。
此时,无数学子恨不得让阿婆主闭上嘴,似乎阿婆主不说了,就不会发生。
【朝臣就问,陛下有什么想法呀。
鹤仙就说,朕觉得孟子与荀子,都是圣贤,只在孔庙从祀,有些太委屈了,朕打算追封二位先贤为圣人,单独建庙祭祀,你们帮朕想想,孟子荀子该称什么圣?】
“陛……殿下大德啊!”
山东,孟家族人此刻,恨不得仰天长啸,高歌一曲,他们祖宗,合该值得一个圣人之位!而且他们孟家家风可比孔家好多了!
孟子在前朝入祀孔庙享受香火,但爵位乃是公爵,哪里比得了圣人?
而在京城参加百家文会的孟怀书等孟家精英,一个个也是激动得不知该如何表达,好日子也是到他们头上了!
圣天子!贤明的圣天子啊!
元泰帝神情恍惚,这就是你的慢慢来?直接改养蛊了?
【林相自然是无脑站鹤仙,鹤仙手里有兵权,武将也忠心于鹤仙。
但问题在于,这件事的矛盾在文人内部,而且,武将也算兵家后人不是?文人一下子多了两个圣人,这还得了?
大多文臣也不愿意呐,看起来是好事,可联想到还没出结果的殿试考题,联想到鹤仙的变法,这分明是想扶持孟子荀子一派的出来拉扯,这能行?
孟子还不是圣人呢,鹤仙就清丈土地,践行民贵了,再以圣人之名为饵,拉拢孟子一派学子,还得了?
最主要的是,儒学内部,本就相互打压得厉害。
所以出现了弘德一朝难得一见的盛景,文武均劝谏鹤仙。】
“卑鄙!”孟怀书低声骂道。
【他们就说,陛下,这不好啊。
荀子主张性恶论,隆礼尊贤而王,重法爱民而霸。虽出身儒家,可思想偏向法家,更有韩非子与李斯两个法家代表的弟子,如何能尊为儒家圣人?
孟子有继承发展孔圣人的理念,但若要与孔圣人并尊,前面还有颜子等几位先贤呢,不妥,不妥。】
“呵,圣人尊位,能者居之,扯什么先后。”
孙平不用扭头,就能想象出好友咬牙切齿的样子。
【出乎意料,这次鹤仙很听劝,表示,那也行吧,就暂时搁置了。】
孙平突然茅塞顿开,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。”
十分想要战斗一番的孟怀书正处于热血上涌中,没太听清:“你说什么?”
“九哥故意的,考题就是为了引起群臣的多思,让他们反对,”姜琦确认道,“九哥装都不装像一点。”
九哥是很听劝的人吗?
也就这群臣子信了,又或者,不得不信。
【但是没过多久,各地就传出各种流言。
比如之所以阻止孟子和荀子被追封圣人,是因为孔家后人有忝祖德,若孟子荀子同为圣人,他们根本比不过孟家与荀氏的子孙,会丢了祖宗的脸。】
“并非流言!”上头的孟怀书已经不去考虑天子的目的了,他只知道,天幕上说得没错!
【这还不算,市民阶层很快涌现出一个声音,既然说荀子偏向法家,还教出了法家的领头人物,那荀子怎么在孔庙,而不是法家圣人呢?】
“噗——”
“你,你不会想把荀子挪出孔庙,真给法家吧?”
又是市民阶层这个词,想也不用想,这就是弘德帝故意放出的风声。
儒生一个个却炸了,“圣人?品德智慧都达到至高境界方为圣人,济世救人方为圣人,法家愚昧百姓,施严刑峻法,如何能出圣人?”
“荀子与圣人之名怎能被法家玷污?!”
可惜天幕不会因此而改变。
【而类似这样的消息,很快就传回了朝堂,鹤仙灵机一动,诶,是个好主意,也不需要和百官商讨了,圣旨一下,在邯郸建造荀庙,追封荀子为法家圣人,将其弟子,毛亨,张苍,以及法家双花韩非子与李斯,都挪到荀庙里去。】
自魏晋之后,早已低调隐居的荀氏后人,在村子里,你看我,我看你,还有这好事儿?在家待着,祖宗就成圣了?
“要出村吗?”
“虽然是利用,可是……”
可是这报酬,未免太丰富了些。
“出!单独建庙祭祀都好说,但法家至今唯一一个被帝王明旨确认的圣人,这样的机会若是错过,百年之后,还有何颜面去见祖宗?”
什么儒家不儒家的,我荀氏就是法家的!
百官感觉脑子嗡嗡的,荀子,成法家圣人了?这合理吗?荀子他老人家知道您乱来吗?
【至于孟子,这样吧,孟家后人与孔家后人比划比划,若是孟家赢了,孟子又怎好再屈居从祀地位?】
“我们已经赢了!”孟怀书红眼,“还能再让殿下给个单独的孟子庙位置吗?”这不是从祀不从祀的问题,这是祖宗尊位的问题!
丁俊捂着自己的牙,有点酸,孔庙从祀都能“屈居”了,真是“委屈”死你孟家了!
【明知是套,但孟家能忍住吗?不能,并且孟家真的赢了,鹤仙有饼是真给啊,孟子荀子都给挪出孔庙,去成圣享单独香火了。
如此一来,不仅儒家内部相争挂到了明面上,重要的是,法家出了个圣人呐,尤其是鹤仙前两年刚试图变法,这背后的含义,还用想?】
【当法家能从儒家拽出一个圣人来,儒家的“唯一正统”性就已经没了,剩下的,不过是交给时间。】
法家得了圣人,自然不会不维护自己的地位,还要防止儒家继续攀咬,将圣人给抢回去。
法家,自古以来,都是君王最好用的利剑,比儒家,好用,能放心用多了,元泰帝心想。
东宫,徐甫不明白,为什么这一期,受伤的是他,而他的师兄,却天降馅饼?
他师兄学的就是荀子和法家思想!
杨春一脸春风得意,干劲满满,跟殿下比起来,他还是太保守了,袖子一捋,“师弟,愣着干什么,干活儿啊!”
这么好的求职环境,怎么能休息呢?
徐甫:……
好想学徐福遁走:)
【自此,儒家一家的垄断被打破,其他学派想要入仕,都要披着儒学皮的情况,也逐渐减少,千年以来,围绕儒家的思想钢印,被撬动了,思想,也迎来了自由。】
这次的视频也不长,但含金量有些太高。
钦明殿内,左相认命地站出来,“陛下,孟子与荀子皆是古之先贤,单独建庙亦是顺应民心,只是……不知荀子庙,该如何定位?”
《孟子》可是科举的必考内容,尊崇孟子的学子更是不知凡凡,若抛开政治目的,只是单纯给孟子建庙称圣,学子是没有不愿的,毕竟学子还单纯。
如今天幕中,既然孟子已经单独成圣,那现世,就得跟上,这对朝廷而言,不是难事。
但最难的,在荀子如何安排,是儒家圣人呢?还是像天幕中一样把人给挪到法家呢?
先前殿下的一手神来之笔,已经把孔家给解决了,百家都已经在“圣君”之名下汇聚在了京城,还需要荀子成法家圣人的骚操作吗?
“陛下,臣以为,荀子应为法家圣人。”大理寺卿石韫玉率先站出来。
天幕都说了,他是太子殿下的人,他都在大理寺了,三法司之一了,他说他是法家的,没人反对吧?
同样想法的陆承霖瞬间跟上,“臣附议,儒家已经有了那么多圣人,给法家一个又怎么了?”
“这是给不给的问题吗?”袁老尚书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,不好对太子发作,还不好对同僚发作吗?
“什么是圣人?圣人并非尊位与虚名,是德行,是操守,是思想的引路人,是明灯。法家呢?只有利益,权术,而全然没有道德,暴秦的例子还在史书上写着呢,法家如何能出圣人?如何担得起圣人?”
“兵家还有兵圣呢,兵戈就和平了?”陆承霖果断拉人下水。
这话一出,武将就不能看戏了,他们武将,还是要学兵法的。
“袁公这话就不对了,一个学派的领路人,集大成者,怎么就担不起圣人尊位了?难不成只允许你儒家有圣人?没这个道理。”
“你兵家都有兵圣了,有你们什么事儿?”
把被拖下水的武将给撅了回去,袁尚书继续对准以陆承霖和石韫玉为代表的“法家”派,“你别给我扯开话题,弘德陛下封法家圣人,是不得已,是为了时局,可现如今并不需要委屈了荀子,自然得就事论事!荀子隆礼重法,是为了引导规劝世人,荀子本心为善,而法家严酷,与荀子之心背道而驰,岂能折辱荀子!”
“法家严酷,是君王所需,而非法家所需,便是如今,治国依旧离不开一个法理,难道本朝的法,尚书觉得严酷吗?”
“你这是狡辩,法家的先贤,有几个是看得到百姓的?把百姓当活生生的人的?毫无仁心!”
“下官觉得,正因如此,荀子才更应为法家圣人,”少有在朝廷发言的林朗站了出来,对袁尚书等荀子该是儒家圣人的上官们拱手道,“荀子主道德教化,因材施教,弟子方能在各方面一展所长,所以能教出两位法家先贤。荀子若为法家圣人,既能让法家学子心服口服,又能让法家学子沐以仁德,此乃两全。”
“儒家弘仁教民,兵家以战止戈,法家推行公正,自当皆有圣人。”
“那也不需要从儒家抢吧!”哪儿有连吃带拿的?荀子又不是只有法家弟子!
这一吵,就停不下来了,逐渐变成多方混战,热闹得堪称过年。
元泰帝看向了鬼点子不少的太子,示意他拿出个主意来,兵家也还是混战进去了。
兵家不是有圣人了吗?不用管,反正不管哪一个皇帝上位,都不可能不用兵家。
只是荀子到底要不要“被”跳槽,姜衡表示,百家文会可以再来一个热闹的课题了,吵吧吵吧,谁有你们会吵啊。
“哎,殿下偏心啊。”
下了朝,儒家的老大人们聚在一起,哀声连连。
儒家享受了纯利千年之久,压得其他学说起不来,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看儒家的笑话,他们还能偏帮儒家不成?
儒家少一个圣人,他们怕是巴不得呢。
“不,无论殿下是何目的,但天幕中追封孟子成圣人是真,提议孟子与荀子为圣人也是真,也就是,若朝臣不反对,殿下真会封。”
只不过换一种玩儿法罢了。
“殿下对先贤,并无什么不满,不满的是当下享受先贤遗泽的‘愚人’。”
“袁公的意思是?”
“荀子我们保不住了,但也不能白白损失一位圣人。”
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圣人之争后,荀子成为法家圣人,荀氏一族随着荀子庙进行迁族,族内的良才入了东宫。
但在儒家的让步之中,重新拟定颜回曾子与子思的爵位封号,颜子复圣公,曾子宗圣公,子思述圣公,虽然还是公,可现在却是“圣公”,没有立马成圣,可态度也很明显了,表现好一点,“公”可能就去掉了。
颜家曾家的后人虽然有些遗憾孟子占了时机越过他们先祖,先行一步追封成圣,但如今这样已经是极好了,谁让孔家那群人太嚣张了呢?
家风,是得再严一些才好,否则,以这位殿下的脾性,定然是让他们实际体会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”的。
自然,这些日子以来,这些人的实力,朝廷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,只等经业书院修建完成,名师便可上任。
当然,这期间,太子也不介意名师们去东宫带带鉴正堂的学生。
没选上老师传道受业的,也不用着急,朝廷正是缺人手的时候,都不白来。
这一晃,就又到了七月,天幕也再次亮了。
【哈哈,有没有想我啊,这一期算是加更了哈,所以这一期也不会太长。】
【我们这一期,主要是说因为变法,鹤仙前后执政风格的变化。】
来了,重点来了,变法。
虽然他们已经猜到了有些内容,毕竟陛下太子已经在让清丈土地了,还让他们拿出合并丁银田赋的章程来。
简单来说,逐步废除人头税,改为土地征税模式,简化税制,减轻少地农民丁银负担,增加世家和地主等的税款,主要是后面这部分,这才是大头。
这哪里是一两年就能施行的……
这简直是个长期性的大工程。
【弘德十二年,彼时鹤仙早已掌控朝堂,军队也握在手中,对外王化战略也稳步进行,又是三十六岁,在皇帝中,也算是年轻有为的阶段。】
“所以你飘了。”元泰帝断言。
姜衡不敢发言,因为这种句式,下面大概率就是转折的部分了,先扬后抑。
【所以,在某一天的朝堂上,林朗突然提出,如今的税法有不妥之处,比如有的百姓已经没有田地,却仍要按照人丁交税,负担太重,又比如底下的官员,会私自巧立名目,多收税银……总之一句话,要变税法。】
元泰帝眉头狂跳,“你让林朗主持变法?”
姜衡心虚。
“满朝文武那么多,你让辅助型丞相给你变法?还敢一来就动命脉?你就找不到一个敢变法的臣子了?”
姜衡垂头。
林朗见状,只能赶紧出列,“陛下,是殿下信任微臣,微臣辜负了殿下……”
“你别替他说话!让他自己说!”元泰帝难得疾言厉色,是真正的生气了。
元泰帝在这儿训子,官员眼观鼻鼻观心,看似认真听着天幕分析变法内容,实则除了负责变法那部分重要臣子,其余的都在分心听太子挨训。
“可能我想着,潜之变法,与我变法无异吧……”
说白了,要主持这个变法,相当于站在了所有士绅豪强世家的对立面,甚至是官僚集团的对立面,他怎么敢轻易交付给他人?
以及,应该是他想着,兵权在手,怎么着,也算实权皇帝,不至于推行不下去。
“呵,与你无异,那你成了吗?”
“……”
“我错了。”
见太子认错,左相便立马给这对父子台阶,“陛下,太子殿下还小,天幕中又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,才稍显经验不足,即使这样,殿下依旧是千古圣君。如今殿下得陛下教导,黄河后的赈灾也办得并无遗漏,可见殿下成长之快,陛下又何必苛责如今的殿下。”
随着左相开口,其他官员也跟着夸赞陛下和太子,元泰帝也没打算真在众人面前教一些不好公开的,听了一通好话,也就顺坡下了。
【林相能力并不差,也没有太多的势力牵扯,又有圣心,若是动的不是“人+地”,或者不一起动,或许还能成功,但一起,饶是林相也有些难以支撑。】
【官员暗戳戳的找麻烦都还是小事,林相不会将这些带到鹤仙面前,官员也不会太过分,毕竟都是在朝堂混的,但是朝堂外就不一样了。】
【弘德十三年,江南考生集体罢考。】
江南考生脸色一白,如今的太子,不会对他们江南区域有意见吧?这可是得了天命的太子……
【鹤仙表示,科举照常进行,江南不考,其他地方的考生多招便是。】
其余各区的考生则面色一喜,这是喜事啊!
元泰帝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【眼见鹤仙态度如此坚决,随之而来的,是江南的商税收不起来。
既得利益者是一张网,严丝合缝,利益共同,他们可以抛出无数个不怕死的商人。
抵制改税,抵制变法。改税法,就是为了把该收的钱收回国库,可当商人集体拒缴,朝廷能杀多少?就算杀了,这样的商人,他们随时可以再堆出来新的。】
“你还不停下来?”
“父皇,要是真就这样停下来,岂不是向他们低头?逼迫得了一次,难道不会有第二次?”太子还没回答,晋王倒是没忍住开了口,“要我看九弟还是脾气太好了,就该都杀咯!”
朝臣心肝儿一颤,还好晋王不是储君,虽然弘德帝还没停下来,挺犟的,但好歹知道不能莽着杀,照晋王这样来,得把江南给逼反呐!
“他们越这样,说明他们越怕,我做得越对。”姜衡虽然站在局势外,知道该各退一步了,但他大概能猜出未来的自己咋想的。
都到这个地步了,天幕中,自己究竟是淌了个怎样的大雷,才能逼迫自己停下来呢?
天幕告诉了他答案,可这代价,有些太大了。
【朝廷要对外用兵,部分区域的军粮需要用到漕运。
都说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不要命的一耽搁,损失的士兵,可绝非杀多少人就能弥补回来的,耽误了战场,更是损失甚大。】